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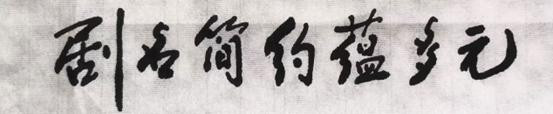
∣邹卫平

孔子曰:“必也正名乎。”所谓: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一部剧集的名字起得好,也能增色和体现整部作品的水准。电视剧《黄雀》的剧名起得就很有创意,蕴涵了多层深刻寓意,既紧扣剧情主题,又隐喻了人性、社会关系和命运博弈的复杂性。
借用了传统的成语典故
该剧名直接化用中国成语“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”,暗示剧中各方势力的博弈关系。在扒窃案件中,受害者(蝉)被扒手(螳螂)盯上,而反扒警察(黄雀)则在暗中观察、伺机抓捕。这种食物链式的隐喻贯穿全剧:扒手团伙作案时,往往也有更高层的“黄雀”(如佛爷)在幕后操控;而警察在追捕过程中,也可能成为犯罪分子锁定的目标。
象征警察的隐蔽行动
反扒警察的工作方式与黄雀的习性相似——隐蔽观察、伺机而动。剧中郭鹏飞等警察常常在火车站人群中潜伏,等待最佳抓捕时机,正如黄雀在暗处等待猎物。编剧王小枪提到:“黄雀是一种很小的鸟”,而男主角名字中的“鹏”与他实际生活的狼狈形成对比,暗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。
人性博弈的隐喻
剧中角色不断在“猎人”与“猎物”的身份间转换。佛爷自诩为最后的“黄雀”,却最终被郭鹏飞抓捕;医生黎小莲看似受控于佛爷,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。
这种攻守关系的流动表明: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,没有人能永远占据“黄雀”的位置,善恶的边界也并非绝对。
社会生态的缩影
该剧以火车站作为主要场景,呈现了一个微型社会生态:扒手、警察、普通旅客构成的食物链,恰如“蝉、螳螂、黄雀”之间的自然法则。剧中多次出现角色观察树上黄雀的镜头,佛爷甚至以此自比,暗示他对权力游戏的掌控欲。
命运的无常与反讽
黄雀的意象也暗含命运的反讽——自以为是的猎手,最终可能成为他人的猎物。佛爷精心布局,却难逃法网;黎小莲试图挣脱命运,仍被卷入更大的漩涡。正如编剧所言:大家年轻时都是理想主义者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“大鹏”,但到最后发现自己就是个黄雀。道出了人生的无奈与宿命感。
意象的颠覆性重构
毛泽东在1965年创作的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中,通过“鲲鹏”与“蓬间雀”的寓言式对话,展现了他对当时国际局势和革命理想的深刻思考。这种“俯瞰寰宇”与“苟安一隅”的对比,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的精神谱系。电视剧《黄雀》的命名与这一意象和谱系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互文与对话,两者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化中关于“鹏与雀”的丰富象征体系。
《黄雀》对传统意象的现代化解构,与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文艺思想一脉相承。剧中火车站作为“蓬间”的具体化场景,使古典意象获得了新的时代生命力。庄子笔下的“小大之辩”经毛泽东转化为革命话语,而《黄雀》又将其下沉为市井警匪故事,这种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转换,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传统。
综上,《黄雀》的剧名不仅是对反扒警察工作特性的精准概括,更成为整部剧探讨人性、权力与社会关系的核心隐喻,使这部警匪剧具备了超越类型的哲学深度。
众和策略-众和策略官网-配资门户导航-网上配资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